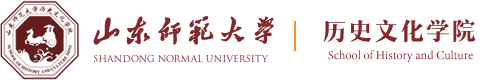一天,校友会的龚老师发我一个微信截图,是他跟一位校友的聊天记录。只见上面写着:96年入学时,最先接触到的课程就有汪老师的课。第一次课堂上,她与我们的心就已经很近很近,下课铃响了,师生们的交流却意犹未尽,汪老师便在黑板上写下7个数字 6868397,说这是她家的电话,有任何事情或需要帮助的,都记得call她。此后她就像大姐姐一样关照着我们班48位同学。说来也很神奇,20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淡忘了,但这7个数字却一直熟记在心,伴随着7个数字留在记忆中的还有亦师亦友的知心大姐姐汪老师。

读着这段文字,我已泪眼婆娑,96级检验班班长董成林的模样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如今他是沪上一家医院的业务骨干和管理者。那个活泼、青涩却故意装成熟的大男孩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想到,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却让他至今铭记在心。其实,若不是他提起,我自己都忘了这个曾经使用过的七位数座机号码。
回想往事,有太多太多的学子令我动容。杏坛耕耘30载,弹指一挥间。曾经的人,曾经的事,教学生涯中的点点滴滴、种种艰辛和乐趣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面对三尺讲台,我也曾有过彷徨,后来却决然坚定了下来,渐渐到如今的执着和狂热,一切皆得益于那些既温顺又叛逆、既勤奋又懒散、既冷静又亢奋的学子们。

江水浩荡,奔流到海不复回;岁月匆匆,青丝变白发,我的锦瑟年华早已依稀难辨。但还记得那年毕业季,我拎着行囊,乘坐公汽来到青山建设一路——美高梅mgm集团2288。放眼望去,四周全是成片成片的菜地和稻荷。我顿时觉得到了乡下,沸腾的热血忽然冷却了,激荡的情怀也不再激荡。原本天马行空的无限遐想,像鸟儿折断了翅膀一般,重重地摔在地上。这一摔便将那个终日沉湎于幻想、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大学生摔回了人间,踏踏实实地接了地气。从此,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已经划上了句号,而充满着种种变数的职业生涯即将开始,我那颗散漫飘荡的灵魂就要在青山安营扎寨了。

建设一路将学校分割成东西两院,东院是教工住宅区,西院是教学重地。我每日便游走在东西两院。当然,闲暇的时候也会沿着建设一路散步到长江南岸,伫立在芳草萋萋的大堤上,眺望北岸商业繁华的汉口高楼。有时雅兴所致,也会顺着江堤东行,来到青山矶,探寻南宋诗人陆游的足迹;抑或访问青山古镇,一睹明朝文学家王世贞“为爱青山矶,且对青山住”的故居遗址。偶尔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带着食材,乘坐渔船,登上武汉最大的江心岛——天兴洲去野炊。也许是青山的美色加速了我由学生到教师角色的转换,我渐渐地爱上了这所坐落在长江岸边、青山矶旁、历经世纪沧桑的高等学府。

当然,一个青年教师要想在高校站稳脚跟,获得学生的认可,仅凭热情或激情几乎等于徒手上青天。为了不至于学生对我评头论足,只得卯足了劲认认真真地备课。还记得初次走上讲台的情景,我对教材烂记于心,精神饱满,信心十足,情绪激昂,侃侃而谈,以极快的语速讲完了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毫无疑问,我对自己的讲解非常满意。
出乎意外的是,一个男生突然站起来向我提问:老师,您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那我想问问您,就我这个具体的人来说,我与月亮上的某一块石头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
我一时语塞,空气骤然紧张起来,瞬间,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嬉笑声。我羞得满面通红,只得搪塞说:你这个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解答不了,课堂时间有限,下次你到办公室去单独回答你。

下课后,我低着头往东院走,还在思考着该如何回答学生的问题。忽然背后有人叫我:小汪,你到办公室去一下。我回头一看,是哲学教研室主任。心里咯噔一下:完了完了,一定是主任偷偷听我课了。刚才在学生面前出洋相全被他看见了,还不知道会怎么批评我呢。像哲学这样的公共必修课,几乎都是三四百学生的大课堂,教研室主任经常悄悄坐在阶梯教室后面听青年教师讲课,然后进行批评指正。
真如雪上加霜,我的情绪更加低落,硬着头皮,忧心忡忡地来到办公室。主任开门见山地问:那个学生的问题,你现在想出答案了吗?我说没有,再想想吧。主任说,你再想也是徒劳,就算你想破脑壳也想不出答案。 我问为什么。他说,学生要你找出他这个人与月亮上某一块石头之间的具体联系,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可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哲学的范畴,是我们哲学学科无法解答的问题,而必须借助于某种具体学科才能解决的。

我仍然一脸的疑惑。主任只得循循善诱地说:你始终要记住哲学只是一门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它仅仅给人们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宏观上指导具体科学的研究,而不能代替具体科学去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我们讲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要让学生树立一种正确的意识,使他懂得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有联系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从而学会发散思维,懂得多视角多立面看待问题,进而达到对事物的全面认识。从宏观上讲,那个学生与月亮上的某块石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但作为他这么一个具体的人与月亮上那个具体的石头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具体联系呢?我们哲学不得而知,那是具体科学的任务,是具体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只有科学家们进行大量的实践实验,并进行反复论证后,才有可能寻找到他们两个具体事物之间的具体联系环节。

听了主任的一番点拨,有如醍醐灌顶,我一下豁然开朗。也终于懂得要站稳讲台,仅仅把教材搞得滚瓜烂熟是远远不够的。后来便猛补短板,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钻研教学方法。关键还要培养学以致用的意识,不能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而应该把理论和实际这两张皮有机地融合起来,将哲学思想融进自己的工作实际、教学实际和生活实际,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辩证思维,经常尝试多视角多立面地全方位认识问题。多年历练之后,我渐渐有了底气,再对学生提出的任何疑难问题,我都能得心应手地解答。即便是个别调皮的学生故意捣乱,我也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掌控局面。

有一次,在我的马哲课堂上,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您今天就不要讲马哲了,给我们讲讲庄子吧,我特别想听庄子的哲学。我说不行啊,必须按教学规划上课。他说,老师您怕什么呢?又没有人知道。我笑问,难道你不是人?他忙调皮地说,对对对,我不是人,这样总可以了吧?
顿时炸开了锅,同学们又是大声嬉笑,又是鼓掌喝彩,还有学生趁机鼓动我说:老师,他都牺牲了一回做人的资格,您就讲讲庄子嘛。我说,不行!他不是人,可我是!众人默然。

但转念一想,这样的对话是不是太过严肃太过生硬?我应该尝试从另一个角度跟同学们进行沟通,使其心服口服才对呀。于是说道:同学们,古今中外,哲学流派有千万家,但老师我只精通马哲这一家。就好比在语文课堂上,学生忽然要求老师证明一个物理定理,老师怎么办?他大概有两种选择,要么拒绝,实事求是地告诉学生,他真不懂物理,不能误导大家。这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负责任的态度。要么为了维护自己的所谓尊严而接受学生的要求,于是便装神弄鬼,不懂装懂,胡编乱造,漏洞百出,将学生带到阴沟里去。我当然不愿做这样的老师。说实话,对于庄子,我只略知皮毛,没有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如果我在这里信口胡诌,鬼话连篇,就会影响到大家对庄子思想的正确认知,这不是一个学者应具有的严谨态度。

台下学生们频频点头,乃至鼓掌。那个发问的学生也站起来诚恳地说,老师,我懂了!此时此刻,我能看出,同学们是真的心悦诚服了。
记得还有一次上课时,坐在后排的两个男生玩手机玩得很开心,竟然笑出声了。我走过去要没收他们的手机,一个男生便嘻嘻哈哈地狡辩:老师,天地良心啊,我们两个真的没有玩游戏,我们是在讨论一个哲学问题。又指着另一个说,是他刚才问我,窗外那个修剪花草的工人是死的还是活的,我说当然是活的,他说不对,我说难道是死的,他说也不对。我被他搞懵了,就打开手机搜索,看看能不能站在哲学的高度来回答他的问题:这个工人究竟是死的还是活的?

另一个连忙附和说:是啊,是啊。辩证法不是讲了吗?要善于从事物的对立面思考问题,好能变坏,坏能变好;福能变祸,祸能变福;长能变短,短能变长;富贵变贫穷,贫穷变富贵。所以呀,你刚才说那个工人是活的,我偏说他是死的,你说他是死的,我就要说他是活的。活与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嘛是不是?你说我把你搞懵了,其实是你没有学好辩证法,不懂矛盾的精髓,所以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了。如果你真正掌握了矛盾规律,那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告诉你吧,那个工人是既死又活,是不死不活。
同学们哄堂大笑。我明知他们瞎胡闹,却没有戳穿他们的谎言。心想,他们没有经过排练,即兴表演竟然如此默契,还真有点小鬼才呢,不服不行啊。但另一方面,我决不允许他们将辩证法作为诡辩的工具。

我转身回到讲台,冷静地扫视了一遍台下的每一位学生,大家顿时安静下来。我调整好情绪,尽可能地用最平和的语气说道:辩证法教我们学会发散思维,学会从多角度看问题,而不是教我们诡辩。人们通常所说的“死”与“活”,是具有严格的生物学意义,是对某一生命个体确切的科学界定,“活”是“活”,“死”就是“死”,绝不存在既“死”又“活”,或“不死不活”,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我想,各位同学一定不需要老师再对这个基本常识做过多的解释了吧。
学生们热烈鼓掌。我也从容地继续授课。待下课铃响后,那两个学生主动走到讲台前向我道歉。我见他们是发自内心地认错,便将手机还给他们了。后来再上课时,却发现他俩坐在了教室的前排。当然,我再也没有看到他们玩手机了。

回想这些令人记忆深刻的学生,心中总是充满了温馨和感动。正是他们的所谓“刁难”、“捣乱”或“诘问”激发了我,历练了我,成就了我。曾经那个充满青春活力、可站在讲台上仍然有些慌张的青涩女教师,已经被学子们打磨得落落大方,沉稳庄重。如今她站在讲台上答疑解惑,娓娓道来;挥舞教鞭,游刃有余。
武科大悠悠一百二十载,很幸运,我没有缺席,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皆融入其中。尽管身体的衰老不可抗拒,但真正的衰老是从心理开始的。在心理上,我时常觉得自己依然年轻,梦想在三尺讲台上再站30年。呵呵,谁知道呢……